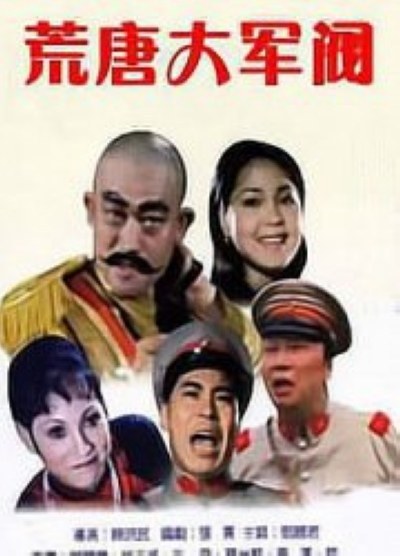- 三三云2
- 三三云1
- HD
- 正片
- 576P

独立时代
- 主演:
- 陈湘琪,陈以文,金燕玲
- 备注:
- 更新576P
- 类型:
- 其他 剧情
- 导演:
- 杨德昌
- 年代:
- 1994
- 地区:
- 香港
- 更新:
- 2024-03-26 10:43
- 简介:
- Birdy(王也明)、Molly(倪淑君)、琪琪(陈湘琪)、小明(王维明)四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做着不同的工作,表面光鲜程度虽有异,都有身份转变(由学生到社会人)时期的尴尬。而这其中最难做人的,是夹在好友Molly与男友小明之间的琪琪,她只能暗自努力,以期好友、男友的事业.....详细
相关其他
独立时代剧情简介
Birdy(王也明)、Molly(倪淑君)、琪琪(陈湘琪)、小明(王维明)四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做着不同的工作,表面光鲜程度虽有异,都有身份转变(由学生到社会人)时期的尴尬。而这其中最难做人的,是夹在好友Molly与男友小明之间的琪琪,她只能暗自努力,以期好友、男友的事业与生活能有所改观,三人的关系能有所改善,却得到双方的误会。
独立时代相关影评
@豆瓣短评
一九六零年代,也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影片素材来源的时代,电影中的小四捅死小明的日子,而在真实的历史里,是一位叫做茅武的中学生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同学,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接近夏日。
就在三十年后,44岁的杨德昌提到茅武杀人事件时说: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不是茅武的生平,或者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人不愿去想那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台湾会有今天,其实跟那个时代非常有关系,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我们那一代在民国五十年(一九六零年代)是念初中,命中注定到民国八十年(一九九零年代)你就是社会中流砥柱。那时候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都会影响到现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年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我希望《牯岭街》除了小孩子看了会开心外,大人看了也能够延伸一些自己的思考: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教训到底在哪里?”
也同样是在1963年,台湾,一部美国电影被当局禁映,名字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编剧和导演也都是美国人,禁映的理由是“会影响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很多在台湾的美国人不是很理解这件事,他们觉得很奇怪:“咦?我们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有趣的电影,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反而不敢面对?”
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粉饰和怯懦,深深压抑着面对内心真实的冲动,看见别人的丑陋,就隐含着自己的丑陋也将被暴露,是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说到人性的丑恶一面,又有多少不同呢?
所以杨德昌当初拍摄《牯岭街》时对观众的盼望并不切实际,首先是小孩子看了不会开心,再者他最为坚定的对个体和群体文化的内省精神,到了大多数成人这里,除了唤起怀旧与伤感,叹息与悲哀,却唯独唤不起自省,为什么?因为即便过了三十年,制度也许改了,生活也许变了,但文化没变,人们内心的压抑并不见得比一百年前少一点,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甚至在21世纪杨德昌的《一一》中,人们对精神出口的渴求也一次次的失败,那样的无所适从已经化为了人和人的同情与心灵深处的孤独。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94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以近乎戏谑的手法与节奏描摹当代台湾众生相,几乎让人看到浑身刺痛,坐立不安,人性背后的动机全部拿到了台前晾晒,一探到底。表面上看,就连最宽容的评论者都觉得,为什么杨德昌镜头下的人物都这么可憎,人与人之间都这么疏离?于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把这种狭隘简单的归结为导演内心的狭隘。
这是可笑的结论,更是观者的悲哀,仿佛中华民族的美德人人都有,而缺德的永远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在银幕上看见美好的情感,就会感同身受,为什么看到丑陋的东西,却想不到那丑陋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所谓的阴暗和美好,本来就应该在阳光下享有同等的对待,一样的坦坦荡荡。否则,我们的文化,从个人到群体,何以谈起自省,何以谈起自信?
实际上这是杨德昌最为真诚的一部电影,把虚伪和所谓的丑陋和美好的情怀一起亮出来给你看,是告诉你:它们同属真实的一部分,无所谓高下,无所谓对错。杨德昌在电影里让我们看到一种正面的态度,无所回避的态度,人性中的道德优劣并不以身份和阶层为界限,也不以穷富来划分,这样正面而强大的价值观念我曾在黑泽明的电影中看到过。就好像这部电影里的富家子弟阿钦,肤浅俗白,事业搞的乱七八糟,成天被人骗,总是喝醉搞不清状况,在影片里出现时是那么令人讨厌,但到最后你发现,他追求自我和爱情的执着比谁都要强烈,也许他不得其法,却努力作出着自己的选择,终究是他最真最单纯。
人是不会改变的吗?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再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不开心之外,会不会在内心产生自发的力量,去抵制那些压抑内心的文化,更开放,更轻松,更正面,更坚持,同时又拥有更加自然多元的宽容度?我相信会的。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是带领了一批几乎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比当时台湾电影工业更健全,更自主的工作环境,用了三年的时间筹备拍摄,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是杨德昌对年轻人最好的信任。
今天,如果让我道出对杨德昌先生最大的敬意,在于尽管并非人人都拥有强力思辨和反省的能力,但因为有了他的电影的出现,就不能说这个文化失去了内省的光芒,这种光芒并非来自高远,而本就该深植在我们心中,内省并非为了转而拿起绳索,去束缚更加年轻的心脏,而是产生自我超越的动力,这超越的动力让我们独自走向精神的开阔之地,并一次次的停下来,感受到灵魂的真实面目,正面了真实还不足够,更在开阔的过程中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他人。
杨德昌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远在美国学电影的台湾朋友打电话来说,无论杨德昌安葬在美国还是台湾,他都会去扫墓。上个世纪的鲁迅先生说,绝望和希望,同样虚妄。是的,在我来看,虚妄既然是人生的底色,也就应该毫无惧色的带着希望去面对,是别无他途的选择。杨德昌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先生相似,既正面人世的真相,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应对真实,这本身已经是美的,即便口出恶言,冷眼以对,即便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与虚伪,也让人感觉到衣服下的心脏比任何人更强烈的盼望着温暖与美好。
所以杨德昌先生的墓碑,在我的想象中,一定是安放在《一一》片头出现的,那么葱郁又茂盛的树下,并且,那将是一个定格的 A Brighter Summer Day。
注明:(杨德昌口述部分引自黄建业先生《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台湾远流出版社)
Liar
原载于 北京青年报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