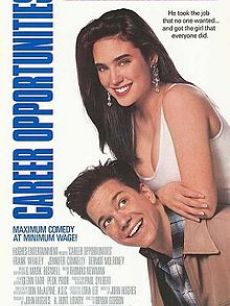大荒来客
- 主演:
- 海娜,王宇辰
- 备注:
- 类型:
- 微电影 喜剧,纪录片
- 导演:
- 殷大卫
- 年代:
- 2012
- 地区:
- 内地
- 更新:
- 2023-08-27 21:09
- 简介:
- 一段古代女娲的搞笑爱情故事,一曲奇异的言行歌,不是常人按常理可以想象的都市冷幽默交响曲,三个不同的都市小人物的爱恨纠葛,值得玩味。网络红极一时的美女“女娲娘娘”出演复古题材微电影《大荒来客》,以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和西单女娲娘娘的“奉献”精神,一个古代女娲的搞笑爱情故事,.....详细
相关微电影
大荒来客剧情简介
一段古代女娲的搞笑爱情故事,一曲奇异的言行歌,不是常人按常理可以想象的都市冷幽默交响曲,三个不同的都市小人物的爱恨纠葛,值得玩味。网络红极一时的美女“女娲娘娘”出演复古题材微电影《大荒来客》,以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和西单女娲娘娘的“奉献”精神,一个古代女娲的搞笑爱情故事,一个奇谈怪论的举动,不是常人按常理可以想象的都市冷幽默交响曲,三个不同的都市小人物的爱恨纠葛,值得玩味。网络红极一时的美女“女娲娘娘”出演复古题材微电影《大荒来客》,以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和西单女娲娘娘的“奉献”精神,
大荒来客相关影评
@豆瓣短评
Bill Maher老师的职业和小沈阳差不多,是个靠电视脱口秀和走穴讲笑话搵钱的。在电视上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之余,他还搞搞公益活动,指导“善待动物协会”拍一些裸女的照片以号召保护动物。
Maher老师这个人很幽默,也很敬业,一个人一生反一次基督不难,难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反基督,还能搞出一部电影来骂基督,这是我们很多无神论者有所不及的。他的Religulous在票房上也相当成功,据说是米国史上第七位最卖座的纪录片,08年最卖座的纪录片。根据盖洛普的跟踪统计,美国大概每十个人里头有9个人自称相信神,有7个人属于某种宗教组织,有6个人每天祈祷,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这个数字一百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在这样一个国家反基督,更是需要相当滴勇气啊。
马老师可能是搞笑帝,勇气帝,但未必是神学帝;电影的票房到位,并不能说明反基督也反到了位。北京的全国劳模,售票员李素丽阿姨,售起票来,真的是让人像心窝子晒着日光机一样,但她前阵子参加鉴黄的“妈妈评审团”,是不是也能评成网评员里的飞行员,就很难说。反低俗的任务是领导布置的,但低俗二字就像个哑谜,低俗的信息砖家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一会儿说是加菲猫,一会儿说是谷歌,你叫李素丽阿姨怎么评。岗位变了,哪怕你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也是不行的。
宗教这个话题太大,我首先还是要从低俗的方面理解。假设有一天,人民币上印的不再是耄的头像而是一句箴言:“我们信春哥”(In Brother Chun We Trust),春哥歌迷会的玉米们宣布曾哥的歌迷为邪恶的异教徒,学校的升旗仪式不再唱国歌而是大喊“信春哥,得永生”,新主席登基不再是对人大代表承诺而是左手按在李宇春的第一张专辑上宣誓,你会有什么感觉?当“中国民主了,会不会选李宇春当总统”这样的问题依然被很多人煞有介事地讨论的时候,你会觉得,以上我所设想的情境似乎也不是离我们那么远。
在马老师眼中,信基督还真就和信春哥差不多。我们来看看他采访的都一些什么货吧:一个过去信撒旦现在改信撒旦他前老板的壮男,一个相信上帝和降雨的龙王没有什么区别的店主,一个猥琐的黑人,宣称自己就是基督。面对他们的一些雷语,美国《娱乐周刊》确实很有娱乐精神地评论道:"The movie is funny as...well, hell."
但是,想一想波普尔所说的吧。经验如果用来证明理论,是永不能穷尽各种可能性的,而无神论也是建立在经验归纳法上的。无神论者说世界上没神,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上,因为他们既不可能考察过世界所有角落,也不一定拥有认识神、找到神的能力,只要有一个神就可以推翻他们的说法了。我若说我哪怕在梦里见过神,你也不能拿着“可我们都没见过神”来说我错,子非我,安知我不知神之安在?幸好,马老师似乎也没说一定没有神,他只是在“怀疑”。
对比《时代精神》(Zeitgeist),《宗教的荒谬》讲的好像不是宗教的荒谬,而是人的愚蠢。宗教学家伊安•巴伯教授抱怨有些科学作家如卡尔•萨根的书中热衷于攻击宗教,但攻击的只是“以通俗的、迷信的形式出现的宗教”,“对有见识的、学院派的神学家们的著作却丝毫未予考虑,而这些人才应该是他所敬仰的科学家在智识上的对手”。当然,《时代精神》也没真正说出多少宗教的荒谬之处,它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埃及神荷鲁斯是多么多么相似,基督传说多么多么符合天文学与占星术原理,却并没说基督信仰本身错在哪里。
实际上,即使在今天这个比尔盖茨比耶稣更有名的时代,科学也没能真正占领上帝的地盘,反而隐藏着至少是与上帝握手言和的可能。上帝早就让科学家们“wow”过了;他们发现,物理常数哪怕有一点很小的变化,都会导致宇宙无法为生物居住。霍金写道:“如果大爆炸之后一秒钟那一刻的膨胀率小上一千亿分之一,那么宇宙在达到其目的的大小之前就会重新坍缩。”除了膨胀率之外,另两个证明宇宙中似乎存在“微调”的例子是元素的形成及粒子的比例。如果核力稍强一点或稍弱一点,稳定的恒星、水或者碳元素便不可能形成。如果早期宇宙中的一百万对质子和反质子配对湮灭后没能留下一个质子,或者留下更多质子,我们的世界也不会出现。霍金老师评论道:“我们的宇宙要从大爆炸这样的事件中浮现出来,其可能性非常之小,我认为(大爆炸)有着明显的宗教意蕴。”(当然,也可以用弱人择原理来解释,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至于量子理论,我们可以说,自然规律仅仅指定了一个潜在性的范围,但是上帝决定了哪种潜在性实际得到实现——所谓的“隐变量”就是上帝。“上帝不掷骰子”,这名言众所周知,可霍金的回应更有意味:“上帝不只是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无神论者还有一些相当好的牌,比如查尔斯•达尔文老师。有人一碰到信徒便祭出达叔当最强召唤兽,孰料进化论也可以是上帝插手过的——化石记录显示,物种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变化相当微小,而在短时期内突然出现了所有已知的进化类群(门),与此前的物种很不相像。有神论者认为,上帝就是在这时候向物种们发出指令的。另有人提出,随机突变不可能产生复杂有机体中存在的许多器官协同起作用的现象,生化系统的“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表明它们不可能是渐进演化的产物。简言之,假设你是只可爱的、毛茸茸的大老鼠,并且敢为天下先,在胳肢窝部位“进化”出一个小翼膜,却没有相应地长出羽毛、龙骨突、用于导航的大脑,则你的翼膜在进化为翅膀之前,首先会成为你上蹿下跳和偷东西时的累赘,让你早于同伴被自然淘汰。再比如,一种新系统,比如老鼠夹,只要有一个弹簧没有发明出来,这整个夹子便是废品——正像眼球的进化若没有相应的复杂神经系统来支撑也是不可成立的。而科学家们指出,指望凭偶然性就产生一组特定的相互作用的蛋白质,不啻于指望人们靠搅动垃圾场里的一堆废金属就造出一家完整的飞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曾经设计出一套计算机程序:在屏幕上显示一些昆虫状的模拟生物,用随机参数来使它们变化,然后用计算机程序预先设定的标准来作选择。他想证明进化是可以在没有目的或没有智能设计的情况下发生,却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事实:偶然性和选择是可以与一位有目的的作用者的智能设计相容的——在此,这位作用者就是计算机程序员。
历史总是这样书写的:科学不断扩张它的领域,上帝则不断割让它的辖地。但是游戏只能这样玩:科学只占领人们暂时确定的领域,无限的未知领域里充满了人们无法解读的道标,上面都写着俩字,“上帝”。可是这位上帝是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斯宾诺莎的上帝”:“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即那位在万物有序的和谐中显示自己的上帝。”
这只是一位自然神论的上帝,或者,“填补空隙的上帝”(God-of-the-gaps):每当我们的知识中出现空隙,我们就对自己说上帝在那里。过去的神学论证只关心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当代基督神学则越来越重视上帝—人—自然三者间的关系。这位上帝和《圣经》里的耶和华好像是有区别的,基督徒怎能接受那位“全知全能”的天主,只是在科学的盲区里敲敲打打呢?——那是因为他们像许多乐观的物理学家一样相信,所有这些看起来为任意的常数,都可以从一个尚不为科学所知的、无所不包的方程中推导出来。而这个方程正是上帝写在天堂的黑板上的。
构成信仰基础的清晰推理并不存在,但是,“有神论并不必然地和科学冲突,它只是和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有冲突。”
即使科学真的不能扳倒上帝,我们还是得承认,Bill Maher等同志津津乐道的死后满状态原地复活和virgin birth对许多人来说确实是扯淡,而全善全能的上帝何以不能消灭恶(“神正论”)这问题也够上帝喝一壶的。就复活问题来说,《圣经》里的见证者并非全是目击证人,更何况还都是耶稣老师的“利害关系人”,这证词真伪如何,还真是有待掂量。就“神正论”问题来说,如果都像电影里那位扮演耶稣的小伙子一样回答:上帝有个人类理解不了的plan,那就和某国的“多难兴邦”那种逻辑差不多,相当于你看见纳粹杀人杀红了眼,却评论道:“德国ZF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神迹的问题上,我更相信国人和这电影有天然的共鸣,身为中国人,已经在这神奇的国土上见识过太多比上帝还有“大能”的奇人铞事。某大湿作“带功报告”,只一声娇叱,便让聋哑人当场说话,近视当场摘掉眼镜,残疾人当场从轮椅上站起来。报告结束,满场扔掉几麻袋的眼镜、香烟、拐杖,耶稣老师看了只有内牛满面的份。耶稣行神迹的时代,别说Handycam了,连录音笔都没有,几个人往羊皮纸上一写就算是见证了。而今天的大湿们通过中科院和人民日报记者的鉴定像玩一样,能治百病的“信息水”还是好多科研机构和大医院化验过的。如今,这些大湿们哪去了?都已经像屁一样地消散了。要说耶稣也是个差不多的大忽悠,不是完全有可能么?
只可惜,拿撒勒那个沧桑而颓废的男人终究不是气功大师,神要救的是你的心灵,神迹又有什么重要,身体的医治又有什么要紧呢?基督看重的是爱,和荣耀神的心,祂衣衫褴褛地在麻风病人中行走不是要cos犀利哥,只为了让你发出“好酷”“好潮”的声音。路德和加尔文早就写:奇迹的时代已结束了,不该再期待奇迹发生。
首先,我们仍得承认,从《死海古卷》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旧约》,与拿撒勒的那个男人在两千年前所读的那本,是如此的接近。在两千年中,圣经基本上被忠实准确地保存下来,这是其它许多著作无法相比的。
其次,即使你人品不太好,素质比较低,就是看信教的不爽,非得恶心他们而后快,你否认不了,小的如突然感到神进入你的世界的奇妙感受,大到保罗登上第三层天或穆圣夜行登霄的奇迹,要为其证伪,可能远比想象的艰难得多。神启是他人内心所见,你无有窥心奇术,怎可力斥其非。耶稣其人其事已是千载遗事,何以绝知其伪。大多数无神论判断是一种对其自身不持批判态度的理性;这种理性主义力求解决有关政治、美学、道德和宗教的全部问题,却仅仅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残破的无神论原教旨大旗无法支撑其偏见百出的证伪之维!
其三,在某种意义上,上帝确实是不可能说明白的。
在传统西方神学中,人们假设能够在自己的思想中认识上帝。一拨又一拨的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安瑟伦、笛卡尔、莱布尼茨)有意避免对自我和世界的经验,假定观念的秩序和真实的秩序完全等同。而在今天,G. Ebeling承认:“上帝”这个词对于今天的人不仅失去了其不言而喻性,甚至失去了其言喻性。虽然美国人中有很多基督信徒,但据甘阳说,成年信徒中一大半人说不出“四福音书”是什么,多数美国人虽然说“十诫”对今天仍有效,却不知道“十诫”究竟是哪“十诫”。
H•奥特承认:“我们不知道在耶稣受难节和耶稣复活节之晨真正‘发生的事情’。作为信仰者,我们不知道它。”但是他说:
与非信仰者在一起,我们虽然可以说:“罗马人把来自拿撒勒的那个男人耶稣钉到十字架上,这会是发生的事情。他的弟子从来误以为看见他活着,这曾是发生的事情。”但这个答覆对于作为信仰者的我们绝对不够。它正好没有表达出信仰在谈到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时所指的。那么信仰(以及作为信仰之思的神学)应该做什么,以便现在说出它真正所指的东西呢?它必须返回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之后并对此与非信仰达成一致,以便在那种东西的后面发掘出本来的历史,即本来发生的事情并且现在对信仰真正至关重要的东西。这类试图合理地重建救恩事件(赎价论、祭罪论等等)的“过程机械主义”的失败使人认识到,将信仰陈述固定在某一层次—它虽然表面是“超自然的”,但原则上却始终脱离不了实证主义的真实概念范畴—这是不可能的。信仰陈述不是这类可以清晰言说的陈述—“它是如此这般”以及“它曾是如此这般”,如像人们描述事物和事实那样;信仰陈述象征地指向不可说的、在最深层触及人的真实。这一点为基督受难和复活的信仰神秘所证实,也为其他一切信仰内容的信仰神秘所证实。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恐怕也必须把上帝的概念或上帝的名字本身理解为象征,因为如果说“存在一个被称为‘上帝’的在者,这是发生的事情”,这大概不甚恰当。通过这种陈述形式,通过这种陈述一理解,“上帝”大概会被造就为一个尘世之内的存在物,而作为上帝的他恰恰不是这种存在物。
换言之,能够证实的上帝还可能是上帝吗?通过这种推理过程,上帝不是被贬低为可以通过人的一点机灵劲儿推测出来的东西了吗?这样的客体化的上帝还是上帝吗?康德使用理论理性通过对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对上帝的证实的方法论所作的批评,不是把上帝存在的证实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吗?
路德思考的问题是“上帝何以是善的?”今天的人们则退后一步,先思考“到底有上帝吗?”可是,给上帝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定义上帝需要一个更高的类概念,但在上帝之上不存在任何更高的类概念。于是有人(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因应康德“为信仰留地盘”的号召提出“教区不重叠”的说法:科学的教区涵盖经验的领域: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事实),它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运行(理论)。而宗教的教区则涉及终极意义和道德价值的问题。每一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规则、标准和判断。如果说对其他领域同样关注人的学者来说,问题主要涉及数据、事实、现象、操作、程序、能量、规范的话,那么,对于神学家来说,问题涉及的是终极的解释、目的、价值、理想、规范、决定、态度。无神论者阿诺德•汤因比写道:“我相信,科学和技术不能作为宗教的代用品,科学技术不能满足各种宗教努力提供的精神需要,虽然科学技术可能损害所谓‘高级宗教’的某些传统教条。在历史上,宗教是先产生的,而科学又从宗教中成长。科学从来没有取代宗教,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取代。”
然而,这样的解答在今天肯定会遭受许多鄙视。我曾在大学自习室碰到那些基督小组的年轻“使徒”们,他们可不管你是在温习还是在泡mm什么的,他们的工作就是用一个钟头的讲演或者一张印满了蝇头小字的传单来告诉你,上帝不仅是阿尔法,是欧米茄,你要是信了祂你还能戴上欧米茄,他们可不敢说上帝是“不可说的”,那样就没人来给社团贡献经费了。
想想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里耶稣的化身John吧,除了永生之外,他就是个凡人,他告诉他的朋友们,其实佛教思想才是基督的源泉。而一心想捍卫基督教尊严的那位女士,除了背诵圣经文本章句之外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申辩,这和我们在许多场合见到的那些蒙上双眼不问经外事,并觉得自己比刘亦菲还圣洁清纯的教徒何其相似。在关于信仰的豆瓣小组里,有那样一些可爱的教友们,不仅不能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反而成了给大家带来智商的优越感的吉祥物,他们声称,他人如果不成为基督徒,便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的存在意义——我们去超市购买猪肉的时候,没有听说售货员要求我们变为猪来感受猪肉真正的价值吧?
对这些童鞋们来说,不管他们是分享真理来的,还是拉人入伙来的,他们要宣讲的信仰也许是超理性的,但是听众的思维却是理性的,如果对任何诘问都像豆瓣小组里的人那样复读一段圣经,绝不会为世界培养什么基督徒,而只能造出些开心果。我,作为一位对猪肉很感兴趣却并不想变身为猪的顾客,依然希望能够以非教徒的身份——哪怕是相当肤浅地——理解宗教的价值。大牛人阿奎那也相信,神学是一种科学,以文字记载的经籍和教会传统便是研究这门学问的基本数据;若要了解有关上帝的知识,信仰和理性的交叉点是必须的。奥古斯丁也相信,“爱知识”的内心思辨之路可以抵达信仰。虽然许多神学家已经不再认可这套说法,但即使当代的宗教研究者(H•奥特)也承认,甚至强调这一点:“诚然,基督教的宣道者必须简明地言说,然而,只有当这种简明为纯粹思的冷峻的严谨和诚实所支撑,它才真正简明、具体。”
一个理性的人,未必会信上帝,信春哥,但他心中的“宗教情感”却总不可消弭的。正如“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说:“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话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宗教认为就是有神论的那些观念、即真正信仰上帝的那些观念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就不会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么,这句话倒完全是真的。这一个意义之下的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很像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切。宗教乃是对于我之所以为我的思量和承认。”康德在实践领域重新划出信仰的地盘,也是由于道德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像自然的实在世界那样,道德世界也有理性秩序的实在性。
只是,由理性人来看,宗教的问答方式是个颠倒的过程,因为答案总是出现在问题之前——上帝是一切的第一原因。而一部“君临在血泊中”的基督教历史也似乎在告诉我们,拥有扭曲的信仰似乎比没信仰更为可怕。当代最有声望的无神论者之一理查德•道金斯写道:“我认为人们有理由说信仰是这个世界上的大恶之一,可以和天花病毒相比,但是却比它更难铲除。信仰作为并非基于证据的信念,是宗教之首恶。……宗教在历史上总是企图回答那些本来属于科学的问题。”
诚然,宗教领袖常常把他们的教条主义立场推广到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之外,但我们更不应忘记,“科学”的达尔文主义也被滥用来为战争、殖民主义、无情的经济剥削和优生学作辩护,引我们走向赫胥黎那个“美丽新世界”。我们更不可把人类想得太客气了,即使没有信仰来回答这些“本来属于科学”的问题,而科学当时又回答不了,就一定会有一些更可怕的傻逼们来回答了。
曾看过一份资料,说是在文革时期,和当时中国所有的民间宗教一样,彝族民间宗教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彝族群众不能随便参与宗教活动。搞笑的是,现在甘洛县彝族群众用汉语称自己的民间宗教时,就叫“迷信”,比如一个人说“我相信彝族的迷信”时,他(或她)指的是相信彝族的民间宗教信仰。宗教何以有这般好,哪怕被说成迷信也要信?人类还真的就是有这么贱,就像马老师一样,他不信上帝,但他总得有什么要信,比如他的“怀疑论”,他信起这个来那份痴迷和虔诚的程度,比起教徒来亦不遑多让。这说明,不管人们囿于各种外部的强制力量还是基于内心的信念无法信仰宗教,心中的宗教情感是不可消灭的。当然,信奉“怀疑”其实是很不错的,对于其他一些“教主”和“信徒”,我们就只能说:哥信的不是信仰,是杯具啊!
中国的先贤们,早已认识到人民需要宗教而西方宗教似乎并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五四的时候,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提出“以礼乐代宗教”,最后好像都没成功,还是让我们今天的共产信仰替代了宗教。勒庞在他《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表现为一种崇拜。”读到这里,我们都要笑而不语,或者哭而不语;因为我们会回想起,我们曾以“亩产十万斤”的稻田让十三亿人吃饱的神迹,让耶稣以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彻底黯然失色。解放前我们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解放后我们马上改口:“某某某是人民的大救星!”
赵汀阳宣布“今天世界上的泛政治意识以及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的后遗症”,并归纳出基督教对精神政治作出的四个发明:心灵管理制度(把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政治问题)、宣传(超现实的美好许诺;简单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话语的无限重复)、群众(心灵高度相似,却未必团结如一人)、绝对敌人(既包括内部敌人,也包括外部敌人)。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今天世俗社会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但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模仿宗教的政治模式上走得太远了。救世主、绝对牺牲、“最高指示”、大量印刷的经文般的读物、教礼般的规章、“异端”、受监视的人民……现代“以人为神”的威权主义者们,先是打倒了这些词汇的主人——宗教,然后又把它们拾起来,并入自己的语汇之中。经过一个世纪的瞎折腾,我们才多少有些明白,谁也没有资格代替上帝对别人颁布精神或肉体的诫命。
照朋霍费尔看来,大约从十三世纪开始人类就逐渐地走向自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得到了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神。”但是自律的结果呢?“与此同时,那些基督教神学的种种世俗的衍生物,即那些生存主义哲学和精神治疗学家,就开始乘虚而入,开始介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他们的著述中向自信、 满足和幸福的人类证明,人类其实是不幸的、绝望的,只有他们可以救你脱离困境。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把人们驱入内心的绝望,然后那就成了人们的绝望。它触及了哪些人呢?一小批知识分子,一小批腐化堕落的人,一小批自以为在世界上最重要并因而喜欢盯着自己的人。”
诚然,我们不会忘记宗教裁判所和火刑,不会忘记宗教信仰被赋予国家强制力之后的可怕,但这完全不是要求信仰退出公共领域。到目前为止,不论在科学理论中还是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缺陷却又不产生其他更坏恶果的一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没有发展起来。不仅是人理性的局限,更是人心灵的缺陷,好像真的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终结”;而以个人智识僭越神之身位的任何努力,泰半堕落为“通往奴役之路”。朋霍费尔诗云:
当你起步追寻自由
你得先学会控制你的感觉和心灵
唯恐你泛滥的情欲和四肢
使你偏离当行的路程
操练你的心灵和肉体唯你是从
好奋力追求你所设定的目标
除非你恒守此律
否则永不得认识自由的秘密
当然,马老师还没有如贵国人民一样傻到去相信威权主义可以代替神,他相信的是——“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要传播的东西。我所散布的福音,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在推销怀疑!这就是我的产品。”我不知道他的怀疑是否将他引入了真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怀疑并不能将他引向任何东西。
刘小枫曾生动地描绘了具有高度理性又有高度德性的,信靠着历史理性(换言之,儒家所谓的“天命”)并相信历史理性可以涤荡一切恶的“诗人”。可是,虽然诗人自愿充当了历史王道中的英雄角色,自居为天命的担当者,却不能为自己的不幸和受苦找出理由:儒家学说说明不了,更担当不了仁人善人总是在受苦的事实。儒家把超验的道德价值建立在历史的、政治的(归根结底,人类之性命的)基础上,却没有顾及人类是否真的具有绝对自足性,于是,“要么把诗人逼上了自杀的绝境,要么把诗人推到了荒诞的墙角”,而“恶统统被掩盖在历史的道德形态之中”。“诗人”、君子以为找到了绝对可靠的“天命”,并由此自以为无所不知,最终却只能感叹“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因为人类被罪湮没的历史一再背离这非神性的“天命”。屈原所祈告的“天”是聋的,它只是自然的自在自为的力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如果它真能说话,它说出的一定是《五号屠场》里Tralfamadore星人那句俗语:So it goes.
可见,并非只有西方人秉有与生俱来的欠缺,并非只有西方历史充满了罪恶,并非只有西方人向神发问。区别在于,中国人认识到历史理性的这种欠缺后,却发明出“无所不能”的“圣王”、“英主”,呼召万民的臣服。
那么,认清了人性的欠缺之后,有没有可能就抱残守缺,像尼采所说一样,amor fati,去爱这虚无、偶然、破碎的世界,从没有根基的土地上发出抗争呢?加缪钟情于周而复始地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并断言“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萨特则说生存的“恶心”正说明人应完全“自由”地自在自为,并称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罗素也说过一番激荡人心的话:「人类的产生,是出自一些漫无目的的来由。人类的起源、发展、盼望、恐惧、爱情、信念,完全是原子盲目冲撞的结果。世上没有任何事物,不管是热诚、英雄本色,理性、或感性,能使他超越坟墓而存续。历代的丰功伟迹,鞠躬尽瘁,雄才大略,以及人类天才登峰造极的成果,迟早要与太阳系同归于尽!人类辉煌成就的殿宇,至终必然埋没在宇宙灰烬的荒冢中!……这些说法,就算并非无可置疑,但却确实到一个地步,任何拒绝这些说法的哲学,是站不住脚的。惟有在这些真理的架构中,在这毫不放松的绝望的稳固根基上,人类才能建造他心灵的住处。」
人真能向绝望发起挑战,甚至以此绝望为根基来建立自己的伟业么?刘小枫对这种“荒诞人”犹不以为然,因为:“它赋予世界的荒诞以应然权利,认可世界的事实性的绝对力量,迫使人的精神情怀与之认同,教人们在荒唐的无聊中心安理得,在无耻中不感到羞耻,在冷漠和随便中不感到难受和痛心……理性用自己的限制把上帝贬到最低限度——无聊,又用同样的限制把经验世界的事实性推到形而上学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来,“荒诞人就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结果:理性的局限不是对它自身的限制,反而是对超验的东西的限制、对一切神圣和美好的东西的限制……理性把自己的局限(不理解超理性的东西),偷换为对神圣的东西的限制(与这个世界不相干)。”“明明是这出于虚无的实存情绪的理智之知不要上帝,却又抱怨没有上帝,进而把自己造成的虚无和恶心的后果归于上帝……有缺陷的理智主动拒斥上帝,并把这种拒斥当作自身确立的首要条件,却又把上帝不存在当做自己受苦的原因……现代虚无主义思想家的‘我思’贼喊捉贼。”
换言之,人类应该正视自己的欠然。首先,正因为这欠然限定了人的自由,人便不可能恣意而行;其次,正是这欠然说明了人有超越的使命和可能,因为它是开放的同义词,是“开放着的无”:
过去,现在,将来
我们都是
无,
那无之玫瑰
无所属之玫瑰
开放着。
(策兰:《无所属之玫瑰》,1963)
这“开放着的无”就是人。我们的生命来自无,走向无;但这无不是空无,而是充盈。它是“创造性的无”,是“恩宠的容器”,是舍勒所说的,“超越的意向和姿态”。
即使我们不以这种有点装逼的角度看待信仰,我们也当发现,现实中时刻都有一些问题要远比老马的“为什么要信上帝”更难以回答。假设有好事者询问中国人:你怎么会没有信仰呢?我们可能会更加难堪。前面已说过,人不可能真的没有信仰,嘴上发誓说“我有信仰我就是猪”,只能说明要么你真正的信仰难以启齿(信钱,信权,信黑社会,信凤姐),要么你处于盲信中而不自知。基督徒有个广告老是搬出来用,说中国之所以没有美国及欧洲富饶,皆因欧美信基督之故,这话已经被很多人举非洲拉美的例子给驳斥了。但我弱弱地想,中国在其他方面上隐性的落后,还是有宗教的原因。
清末的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曾很傻很天真地以为,西方文明只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器用之学”,而我天朝虽然贫弱,却颇得孔孟的道德哲学之根本,因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好像说,别看你们现在这么牛逼,不过是些有钱没文化的煤老板;等有一天你们在荒淫中得了花柳奄奄一息,我们就会拿起四书五经去拯救你们,我们才是真正的动感超人,哈哈哈——只可惜这种阿Q的精神只是当年对西方认识不多的产物,自严复等人驳斥后逐渐无人问津。陈寅恪先生反而批评中国文化太重“实用”:“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
早在1920 年2 月1 日,陈独秀就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该文认为,耶稣教给我们的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这精神“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我党先驱李大钊也认为:“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蓝公武先生,则著有《宗教建设论》一书,认为“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然今之宗教,不一二数,曰儒,曰佛,曰耶,曰回,其教义虽互有异同,而皆足以起人之奉,坚人之信仰……使其而一有效者,则佛可以救国,儒可以救国,即耶、回诸教,亦无一不足以救国。”前面说的寅恪先生,则对佛教大有好感:“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后来既视佛教为垃圾,也视基督为乐色;既没能选择全面保守,也没有选择“全盘西化”,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盘西化——苏联化。(或者说,是苏联化选择了我们囧)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反而看到,似乎中国人才成了那个为利益不惜出卖良心的煤老板,而欧美人关心的**、**和**等“普世价值”,要么被我们视为不怀好意,要么被我们划入敏感词。“民主的细节”,成了离我们很遥远的事,但我们毕竟看到,原来西方以基督精神为代表的道德哲学远不是我们所想的那般孱弱,它没有沦陷在纸醉金迷的工业文明之中,它可以巨浪滔天,也可以润物无声,无数普通人将它薪火相传,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善人都被关入牢狱,孤苦无告时,它仍然不绝地回应着西方人在心灵旷野上的切切呼告,护持着他们爱怜每份穷苦和良善的心,而这一切,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
在《论基督徒》中,汉斯•昆提出了一段我相信任何人都难以辩驳的话:“必须终止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里人民大众被贬低、被蔑视、遭受贫困和剥削;最高的价值是商品价值,货币是真正的上帝,行动的动机是利润、一己利益、自私的目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发挥着宗教代用品的功能。”
这描述的似乎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到今天,各种歌舞升平的盛世假象已经很难掩盖这个大国如索多玛般的内核,更无法搪塞这一事实:“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一个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理念对于中国是合适的,也不知道如何知道什么理念对中国是合适的(赵汀阳)。”威廉•詹姆斯讲,宗教是“个体在孤独的状态中,当他认为自身与其所认定的神圣对象有某种关系时的感觉、行动与经验”。 我们中国人,正是被幸福指数最高,被寂寞指数也最高的一群;那些无奈的事,听多了,看多了,老百姓就学会了健忘,懂得了孤独。说实在的,不想孤独也难,那样就会沦为“不明真相”或“不法分子”的一员。
那么,基督教对于我们是合适的吗?对于中国来说,基督和孔子有些什么不同的意味?上帝和春哥又有哪些不同呢?汉斯•昆曾自我发问道:“基督教面对着后基督教的各种人道主义,有进化论的或者革命的,这些主义也同样支持一切真善美,赞同一切人类价值和博爱,以及自由平等……如果是这样,或者至少应该这样,那么基督教还有什么特殊?”
他说,回答很简单——
一、 基督教的特征是耶稣本身,他不断得到重新的认识被承认为救主。
二、 进化论或革命论的人道主义偶尔地无论怎样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尊敬,甚至把他当作榜样,都不会在人的全部维度中把他视为对人具有最终决定性的、限定性的和原型的意义。
昆老师高屋建瓴,我呢就不一定解释得好这些话的意思,只能大致说说。就儒学来说,孔子的“仁”虽然很有希望成为中国人所能信靠的终极价值,但邓晓芒老师指出,一部《论语》并没有真正地说清楚“仁”是什么(要么答非所问,要么意旨不明,要么过于简单);儒家主要是一套实用性的伦理规范,而且还是一套不够全面的伦理规范。“山上宝训”道:“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确实狠了点,但是“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这种一会论心一会论迹的做法又让民间的道德标准过于灵活而失去制约力。孔子又是一位不容对话的教主,他的学生们只能谦卑地领受他的思想,而不能对他有任何质疑。邓晓芒由此认为,儒家的言说方式只能导向一个父权专制的制度,对信念的依托与对强权的依托成为一体。
而耶稣基督则首先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出现的,舍斯托夫引述路德的话说:“上帝派自己的独生子去尘世,并把一切罪恶加之于他身上,说:你是彼得,一个离经叛道者,你是保罗,一个强暴者和渎神者,你是大卫,一个私通者,你是偷吃天堂之苹果的罪犯,你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你犯了尘世中所有的罪。”从每个人都是欠缺的前提出发,耶稣平等对待每个人,鼓励着每个人与祂对话。
更重要的是,如赵汀阳老师说,“(儒家)只说明了一种社会秩序,却根本没有设计出生活的诱惑和意义。假如一种伦理体系不能蕴涵某种精神性的诱惑,它就不是一种足够好的伦理。儒家最主要的观念是一种父权专制制度,即在家庭的事务上完全服从父亲,在社会事务上完全服从皇帝。这也许是有效的管理方式,可是把人管理好了到底是又想让人去做什么呢?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可能生活?儒家的缺陷正在于它把这种伦理制度本身当成了最高价值,于是,这种伦理观念就不是用来追求其它价值的,而是用来追求伦理自身,这种自相关的伦理是一种严重的理论缺陷,一种不服务于其它精神价值的伦理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而且它实际上压抑了人们关于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的想象和追求。如果没有某种优越的精神追求,规范就没有价值分量,人们所想象的好生活就无非是物质享受。”
儒家找不到真正的精神价值,正是在于它是完全立足于尘世的,而终极价值只能向不可能的地方寻觅,在不可言说的地方言说。就汉斯•昆看来,当现代以来的上帝脱去了天真的、人类学的外衣,祂已不是一种“光明的”、神的映像,而更多地是对现实的一种统一的理解:是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上帝交出的终极价值便是“爱”,祂要求着你以爱来回应。
上帝和春哥的区别正在这里,你没必要信春哥是因为你知道春哥只是个唱歌的,一打开芒果台就能看到,春哥身上没有不可言喻的神性;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并非她的经纪人、老板、作曲者、保姆、亲人、或曾哥,她就对你没有爱。对于没有神性的存在,我们不能去信仰,而只需去认识;如果能以短信方式给她投票,那就做得更到位了。可是上帝是无法认识的,因为祂即使不一定真是全知、全能、全善,祂也必如缪勒(Max Muller)所言:“上帝的概念无论可能是何等的不完善,多么的幼稚,它总是代表了人类灵魂在当时所能把握的无上完善的理想。”
因此,今天我们考察宗教的效能,不会单单去看它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更要看它能指引怎样的实践。王守仁讲知行合一,唯物主义者也鼓掌,因为“不能实践的空想什么的最讨厌了!”可是“行”并不是只能绑在“知”的大腿上,因为人并不都是理性的,理性人是研究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却不会只按理性行事,爱因斯坦指出:“在所有高级的科学工作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信念,即相信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制度善于威慑人让人不做什么,可是只有非理性的爱和希望,才能激励人们做什么,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即是说,很多时候,只有“信”才能导致“行”。对有的信徒来说,救恩是预定的,我的事功并不能换来上帝青眼相看,但是真正理解上帝之恩典的信徒必定会做些事情来改良这个社会,因为“神助自助者”。
在今天的中国,不缺乏真知灼见的人,多数人都知道民主自由是好的,但考虑到自我利益,他们宁可放弃对这些敏感词的追求,因为“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我怎么知道实现民主的赔率是多少?会不会幸福都被你们这些孙子享受了,痛苦都撞我头上了?是以你知得再清楚,仍然不会去行。对更审时度势的人来说,所谓平等、正义、自由,这些概念是根本无法以理性考量来证明的。到最后,再多的被代表和被自杀都已不能让我们动容,最多只会“画个圈圈诅咒你”。而对美国人来说,信仰早已给出确定的依靠了:“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
热衷于死啃《圣经》原本的机要论者和在修道院中终老一生的圣者们已不再是今天教徒的主要面貌。汉斯•昆说:“对上帝的理解的前提是现代意识从注重来世转向注重现在:作为世俗化过程的结果,尘世各种体系的自主性不仅在理论上日益为人所知,而且在实践上也化为现实。但是,放弃来世许诺和更密切注视现世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机会:生活虽然可能失去了某种深度,但可能增加其强度。”而今天的世界,在克服了宗教专制主义之后,面对着更深刻的堕入世俗主义的危机;上帝对于实践的价值,仍然是祂作为固有的超验的价值。
克尔凯郭尔早已说了,“如果我能客观地把握到上帝,我就不可能有信仰。正是我不能,所以才必须有信仰。”舍斯托夫从他的灵魂里听到了绝望而最可宝贵的旷野呼告,坚信世人要“以头撞墙”。正因为这种真理荒谬,它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我才肯定。
所以,你尽可说,“《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却不能忽视艾略特的信念:
“我们的启示价值论主张:任何书要拥有这种价值的话,必须是在不自主,即不出于作者之自由意志的情况下编撰成,或是主张这种书不能有任何科学或历史的错误,也不能表达任何区域性或个人的情感,否则,《圣经》也许就会在我们手中得到不适当的对待。
相反,如果我们的理论承认:一本书还是可以成为一部启示,虽然含有错误、感情以及人为刻意的创作,只要它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与其命运的危机搏斗之内在经验的真实记录,我们就可以对它作出较为有利的判断。”
哥信的是上帝,不是寂寞。
P.S.1: 请全知全能的友邻们不吝指正。请剽窃者自重。
P.S.2: 豆瓣诸信仰讨论小组对此文亦有贡献。
P.S.3: 还有许多想法此处已无空间吐露,读者诸君,我们还是留待下回分解吧。
Maher老师这个人很幽默,也很敬业,一个人一生反一次基督不难,难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反基督,还能搞出一部电影来骂基督,这是我们很多无神论者有所不及的。他的Religulous在票房上也相当成功,据说是米国史上第七位最卖座的纪录片,08年最卖座的纪录片。根据盖洛普的跟踪统计,美国大概每十个人里头有9个人自称相信神,有7个人属于某种宗教组织,有6个人每天祈祷,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这个数字一百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在这样一个国家反基督,更是需要相当滴勇气啊。
马老师可能是搞笑帝,勇气帝,但未必是神学帝;电影的票房到位,并不能说明反基督也反到了位。北京的全国劳模,售票员李素丽阿姨,售起票来,真的是让人像心窝子晒着日光机一样,但她前阵子参加鉴黄的“妈妈评审团”,是不是也能评成网评员里的飞行员,就很难说。反低俗的任务是领导布置的,但低俗二字就像个哑谜,低俗的信息砖家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一会儿说是加菲猫,一会儿说是谷歌,你叫李素丽阿姨怎么评。岗位变了,哪怕你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也是不行的。
宗教这个话题太大,我首先还是要从低俗的方面理解。假设有一天,人民币上印的不再是耄的头像而是一句箴言:“我们信春哥”(In Brother Chun We Trust),春哥歌迷会的玉米们宣布曾哥的歌迷为邪恶的异教徒,学校的升旗仪式不再唱国歌而是大喊“信春哥,得永生”,新主席登基不再是对人大代表承诺而是左手按在李宇春的第一张专辑上宣誓,你会有什么感觉?当“中国民主了,会不会选李宇春当总统”这样的问题依然被很多人煞有介事地讨论的时候,你会觉得,以上我所设想的情境似乎也不是离我们那么远。
在马老师眼中,信基督还真就和信春哥差不多。我们来看看他采访的都一些什么货吧:一个过去信撒旦现在改信撒旦他前老板的壮男,一个相信上帝和降雨的龙王没有什么区别的店主,一个猥琐的黑人,宣称自己就是基督。面对他们的一些雷语,美国《娱乐周刊》确实很有娱乐精神地评论道:"The movie is funny as...well, hell."
但是,想一想波普尔所说的吧。经验如果用来证明理论,是永不能穷尽各种可能性的,而无神论也是建立在经验归纳法上的。无神论者说世界上没神,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上,因为他们既不可能考察过世界所有角落,也不一定拥有认识神、找到神的能力,只要有一个神就可以推翻他们的说法了。我若说我哪怕在梦里见过神,你也不能拿着“可我们都没见过神”来说我错,子非我,安知我不知神之安在?幸好,马老师似乎也没说一定没有神,他只是在“怀疑”。
对比《时代精神》(Zeitgeist),《宗教的荒谬》讲的好像不是宗教的荒谬,而是人的愚蠢。宗教学家伊安•巴伯教授抱怨有些科学作家如卡尔•萨根的书中热衷于攻击宗教,但攻击的只是“以通俗的、迷信的形式出现的宗教”,“对有见识的、学院派的神学家们的著作却丝毫未予考虑,而这些人才应该是他所敬仰的科学家在智识上的对手”。当然,《时代精神》也没真正说出多少宗教的荒谬之处,它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埃及神荷鲁斯是多么多么相似,基督传说多么多么符合天文学与占星术原理,却并没说基督信仰本身错在哪里。
实际上,即使在今天这个比尔盖茨比耶稣更有名的时代,科学也没能真正占领上帝的地盘,反而隐藏着至少是与上帝握手言和的可能。上帝早就让科学家们“wow”过了;他们发现,物理常数哪怕有一点很小的变化,都会导致宇宙无法为生物居住。霍金写道:“如果大爆炸之后一秒钟那一刻的膨胀率小上一千亿分之一,那么宇宙在达到其目的的大小之前就会重新坍缩。”除了膨胀率之外,另两个证明宇宙中似乎存在“微调”的例子是元素的形成及粒子的比例。如果核力稍强一点或稍弱一点,稳定的恒星、水或者碳元素便不可能形成。如果早期宇宙中的一百万对质子和反质子配对湮灭后没能留下一个质子,或者留下更多质子,我们的世界也不会出现。霍金老师评论道:“我们的宇宙要从大爆炸这样的事件中浮现出来,其可能性非常之小,我认为(大爆炸)有着明显的宗教意蕴。”(当然,也可以用弱人择原理来解释,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至于量子理论,我们可以说,自然规律仅仅指定了一个潜在性的范围,但是上帝决定了哪种潜在性实际得到实现——所谓的“隐变量”就是上帝。“上帝不掷骰子”,这名言众所周知,可霍金的回应更有意味:“上帝不只是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无神论者还有一些相当好的牌,比如查尔斯•达尔文老师。有人一碰到信徒便祭出达叔当最强召唤兽,孰料进化论也可以是上帝插手过的——化石记录显示,物种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变化相当微小,而在短时期内突然出现了所有已知的进化类群(门),与此前的物种很不相像。有神论者认为,上帝就是在这时候向物种们发出指令的。另有人提出,随机突变不可能产生复杂有机体中存在的许多器官协同起作用的现象,生化系统的“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表明它们不可能是渐进演化的产物。简言之,假设你是只可爱的、毛茸茸的大老鼠,并且敢为天下先,在胳肢窝部位“进化”出一个小翼膜,却没有相应地长出羽毛、龙骨突、用于导航的大脑,则你的翼膜在进化为翅膀之前,首先会成为你上蹿下跳和偷东西时的累赘,让你早于同伴被自然淘汰。再比如,一种新系统,比如老鼠夹,只要有一个弹簧没有发明出来,这整个夹子便是废品——正像眼球的进化若没有相应的复杂神经系统来支撑也是不可成立的。而科学家们指出,指望凭偶然性就产生一组特定的相互作用的蛋白质,不啻于指望人们靠搅动垃圾场里的一堆废金属就造出一家完整的飞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曾经设计出一套计算机程序:在屏幕上显示一些昆虫状的模拟生物,用随机参数来使它们变化,然后用计算机程序预先设定的标准来作选择。他想证明进化是可以在没有目的或没有智能设计的情况下发生,却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事实:偶然性和选择是可以与一位有目的的作用者的智能设计相容的——在此,这位作用者就是计算机程序员。
历史总是这样书写的:科学不断扩张它的领域,上帝则不断割让它的辖地。但是游戏只能这样玩:科学只占领人们暂时确定的领域,无限的未知领域里充满了人们无法解读的道标,上面都写着俩字,“上帝”。可是这位上帝是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斯宾诺莎的上帝”:“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即那位在万物有序的和谐中显示自己的上帝。”
这只是一位自然神论的上帝,或者,“填补空隙的上帝”(God-of-the-gaps):每当我们的知识中出现空隙,我们就对自己说上帝在那里。过去的神学论证只关心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当代基督神学则越来越重视上帝—人—自然三者间的关系。这位上帝和《圣经》里的耶和华好像是有区别的,基督徒怎能接受那位“全知全能”的天主,只是在科学的盲区里敲敲打打呢?——那是因为他们像许多乐观的物理学家一样相信,所有这些看起来为任意的常数,都可以从一个尚不为科学所知的、无所不包的方程中推导出来。而这个方程正是上帝写在天堂的黑板上的。
构成信仰基础的清晰推理并不存在,但是,“有神论并不必然地和科学冲突,它只是和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有冲突。”
即使科学真的不能扳倒上帝,我们还是得承认,Bill Maher等同志津津乐道的死后满状态原地复活和virgin birth对许多人来说确实是扯淡,而全善全能的上帝何以不能消灭恶(“神正论”)这问题也够上帝喝一壶的。就复活问题来说,《圣经》里的见证者并非全是目击证人,更何况还都是耶稣老师的“利害关系人”,这证词真伪如何,还真是有待掂量。就“神正论”问题来说,如果都像电影里那位扮演耶稣的小伙子一样回答:上帝有个人类理解不了的plan,那就和某国的“多难兴邦”那种逻辑差不多,相当于你看见纳粹杀人杀红了眼,却评论道:“德国ZF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神迹的问题上,我更相信国人和这电影有天然的共鸣,身为中国人,已经在这神奇的国土上见识过太多比上帝还有“大能”的奇人铞事。某大湿作“带功报告”,只一声娇叱,便让聋哑人当场说话,近视当场摘掉眼镜,残疾人当场从轮椅上站起来。报告结束,满场扔掉几麻袋的眼镜、香烟、拐杖,耶稣老师看了只有内牛满面的份。耶稣行神迹的时代,别说Handycam了,连录音笔都没有,几个人往羊皮纸上一写就算是见证了。而今天的大湿们通过中科院和人民日报记者的鉴定像玩一样,能治百病的“信息水”还是好多科研机构和大医院化验过的。如今,这些大湿们哪去了?都已经像屁一样地消散了。要说耶稣也是个差不多的大忽悠,不是完全有可能么?
只可惜,拿撒勒那个沧桑而颓废的男人终究不是气功大师,神要救的是你的心灵,神迹又有什么重要,身体的医治又有什么要紧呢?基督看重的是爱,和荣耀神的心,祂衣衫褴褛地在麻风病人中行走不是要cos犀利哥,只为了让你发出“好酷”“好潮”的声音。路德和加尔文早就写:奇迹的时代已结束了,不该再期待奇迹发生。
首先,我们仍得承认,从《死海古卷》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旧约》,与拿撒勒的那个男人在两千年前所读的那本,是如此的接近。在两千年中,圣经基本上被忠实准确地保存下来,这是其它许多著作无法相比的。
其次,即使你人品不太好,素质比较低,就是看信教的不爽,非得恶心他们而后快,你否认不了,小的如突然感到神进入你的世界的奇妙感受,大到保罗登上第三层天或穆圣夜行登霄的奇迹,要为其证伪,可能远比想象的艰难得多。神启是他人内心所见,你无有窥心奇术,怎可力斥其非。耶稣其人其事已是千载遗事,何以绝知其伪。大多数无神论判断是一种对其自身不持批判态度的理性;这种理性主义力求解决有关政治、美学、道德和宗教的全部问题,却仅仅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残破的无神论原教旨大旗无法支撑其偏见百出的证伪之维!
其三,在某种意义上,上帝确实是不可能说明白的。
在传统西方神学中,人们假设能够在自己的思想中认识上帝。一拨又一拨的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安瑟伦、笛卡尔、莱布尼茨)有意避免对自我和世界的经验,假定观念的秩序和真实的秩序完全等同。而在今天,G. Ebeling承认:“上帝”这个词对于今天的人不仅失去了其不言而喻性,甚至失去了其言喻性。虽然美国人中有很多基督信徒,但据甘阳说,成年信徒中一大半人说不出“四福音书”是什么,多数美国人虽然说“十诫”对今天仍有效,却不知道“十诫”究竟是哪“十诫”。
H•奥特承认:“我们不知道在耶稣受难节和耶稣复活节之晨真正‘发生的事情’。作为信仰者,我们不知道它。”但是他说:
与非信仰者在一起,我们虽然可以说:“罗马人把来自拿撒勒的那个男人耶稣钉到十字架上,这会是发生的事情。他的弟子从来误以为看见他活着,这曾是发生的事情。”但这个答覆对于作为信仰者的我们绝对不够。它正好没有表达出信仰在谈到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时所指的。那么信仰(以及作为信仰之思的神学)应该做什么,以便现在说出它真正所指的东西呢?它必须返回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之后并对此与非信仰达成一致,以便在那种东西的后面发掘出本来的历史,即本来发生的事情并且现在对信仰真正至关重要的东西。这类试图合理地重建救恩事件(赎价论、祭罪论等等)的“过程机械主义”的失败使人认识到,将信仰陈述固定在某一层次—它虽然表面是“超自然的”,但原则上却始终脱离不了实证主义的真实概念范畴—这是不可能的。信仰陈述不是这类可以清晰言说的陈述—“它是如此这般”以及“它曾是如此这般”,如像人们描述事物和事实那样;信仰陈述象征地指向不可说的、在最深层触及人的真实。这一点为基督受难和复活的信仰神秘所证实,也为其他一切信仰内容的信仰神秘所证实。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恐怕也必须把上帝的概念或上帝的名字本身理解为象征,因为如果说“存在一个被称为‘上帝’的在者,这是发生的事情”,这大概不甚恰当。通过这种陈述形式,通过这种陈述一理解,“上帝”大概会被造就为一个尘世之内的存在物,而作为上帝的他恰恰不是这种存在物。
换言之,能够证实的上帝还可能是上帝吗?通过这种推理过程,上帝不是被贬低为可以通过人的一点机灵劲儿推测出来的东西了吗?这样的客体化的上帝还是上帝吗?康德使用理论理性通过对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对上帝的证实的方法论所作的批评,不是把上帝存在的证实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吗?
路德思考的问题是“上帝何以是善的?”今天的人们则退后一步,先思考“到底有上帝吗?”可是,给上帝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定义上帝需要一个更高的类概念,但在上帝之上不存在任何更高的类概念。于是有人(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因应康德“为信仰留地盘”的号召提出“教区不重叠”的说法:科学的教区涵盖经验的领域: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事实),它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运行(理论)。而宗教的教区则涉及终极意义和道德价值的问题。每一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规则、标准和判断。如果说对其他领域同样关注人的学者来说,问题主要涉及数据、事实、现象、操作、程序、能量、规范的话,那么,对于神学家来说,问题涉及的是终极的解释、目的、价值、理想、规范、决定、态度。无神论者阿诺德•汤因比写道:“我相信,科学和技术不能作为宗教的代用品,科学技术不能满足各种宗教努力提供的精神需要,虽然科学技术可能损害所谓‘高级宗教’的某些传统教条。在历史上,宗教是先产生的,而科学又从宗教中成长。科学从来没有取代宗教,而且我希望永远也不取代。”
然而,这样的解答在今天肯定会遭受许多鄙视。我曾在大学自习室碰到那些基督小组的年轻“使徒”们,他们可不管你是在温习还是在泡mm什么的,他们的工作就是用一个钟头的讲演或者一张印满了蝇头小字的传单来告诉你,上帝不仅是阿尔法,是欧米茄,你要是信了祂你还能戴上欧米茄,他们可不敢说上帝是“不可说的”,那样就没人来给社团贡献经费了。
想想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里耶稣的化身John吧,除了永生之外,他就是个凡人,他告诉他的朋友们,其实佛教思想才是基督的源泉。而一心想捍卫基督教尊严的那位女士,除了背诵圣经文本章句之外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申辩,这和我们在许多场合见到的那些蒙上双眼不问经外事,并觉得自己比刘亦菲还圣洁清纯的教徒何其相似。在关于信仰的豆瓣小组里,有那样一些可爱的教友们,不仅不能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反而成了给大家带来智商的优越感的吉祥物,他们声称,他人如果不成为基督徒,便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的存在意义——我们去超市购买猪肉的时候,没有听说售货员要求我们变为猪来感受猪肉真正的价值吧?
对这些童鞋们来说,不管他们是分享真理来的,还是拉人入伙来的,他们要宣讲的信仰也许是超理性的,但是听众的思维却是理性的,如果对任何诘问都像豆瓣小组里的人那样复读一段圣经,绝不会为世界培养什么基督徒,而只能造出些开心果。我,作为一位对猪肉很感兴趣却并不想变身为猪的顾客,依然希望能够以非教徒的身份——哪怕是相当肤浅地——理解宗教的价值。大牛人阿奎那也相信,神学是一种科学,以文字记载的经籍和教会传统便是研究这门学问的基本数据;若要了解有关上帝的知识,信仰和理性的交叉点是必须的。奥古斯丁也相信,“爱知识”的内心思辨之路可以抵达信仰。虽然许多神学家已经不再认可这套说法,但即使当代的宗教研究者(H•奥特)也承认,甚至强调这一点:“诚然,基督教的宣道者必须简明地言说,然而,只有当这种简明为纯粹思的冷峻的严谨和诚实所支撑,它才真正简明、具体。”
一个理性的人,未必会信上帝,信春哥,但他心中的“宗教情感”却总不可消弭的。正如“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说:“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话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宗教认为就是有神论的那些观念、即真正信仰上帝的那些观念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就不会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么,这句话倒完全是真的。这一个意义之下的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很像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切。宗教乃是对于我之所以为我的思量和承认。”康德在实践领域重新划出信仰的地盘,也是由于道德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像自然的实在世界那样,道德世界也有理性秩序的实在性。
只是,由理性人来看,宗教的问答方式是个颠倒的过程,因为答案总是出现在问题之前——上帝是一切的第一原因。而一部“君临在血泊中”的基督教历史也似乎在告诉我们,拥有扭曲的信仰似乎比没信仰更为可怕。当代最有声望的无神论者之一理查德•道金斯写道:“我认为人们有理由说信仰是这个世界上的大恶之一,可以和天花病毒相比,但是却比它更难铲除。信仰作为并非基于证据的信念,是宗教之首恶。……宗教在历史上总是企图回答那些本来属于科学的问题。”
诚然,宗教领袖常常把他们的教条主义立场推广到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之外,但我们更不应忘记,“科学”的达尔文主义也被滥用来为战争、殖民主义、无情的经济剥削和优生学作辩护,引我们走向赫胥黎那个“美丽新世界”。我们更不可把人类想得太客气了,即使没有信仰来回答这些“本来属于科学”的问题,而科学当时又回答不了,就一定会有一些更可怕的傻逼们来回答了。
曾看过一份资料,说是在文革时期,和当时中国所有的民间宗教一样,彝族民间宗教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彝族群众不能随便参与宗教活动。搞笑的是,现在甘洛县彝族群众用汉语称自己的民间宗教时,就叫“迷信”,比如一个人说“我相信彝族的迷信”时,他(或她)指的是相信彝族的民间宗教信仰。宗教何以有这般好,哪怕被说成迷信也要信?人类还真的就是有这么贱,就像马老师一样,他不信上帝,但他总得有什么要信,比如他的“怀疑论”,他信起这个来那份痴迷和虔诚的程度,比起教徒来亦不遑多让。这说明,不管人们囿于各种外部的强制力量还是基于内心的信念无法信仰宗教,心中的宗教情感是不可消灭的。当然,信奉“怀疑”其实是很不错的,对于其他一些“教主”和“信徒”,我们就只能说:哥信的不是信仰,是杯具啊!
中国的先贤们,早已认识到人民需要宗教而西方宗教似乎并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五四的时候,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宗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提出“以礼乐代宗教”,最后好像都没成功,还是让我们今天的共产信仰替代了宗教。勒庞在他《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道:“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表现为一种崇拜。”读到这里,我们都要笑而不语,或者哭而不语;因为我们会回想起,我们曾以“亩产十万斤”的稻田让十三亿人吃饱的神迹,让耶稣以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神迹彻底黯然失色。解放前我们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解放后我们马上改口:“某某某是人民的大救星!”
赵汀阳宣布“今天世界上的泛政治意识以及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的后遗症”,并归纳出基督教对精神政治作出的四个发明:心灵管理制度(把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政治问题)、宣传(超现实的美好许诺;简单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叙事;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话语的无限重复)、群众(心灵高度相似,却未必团结如一人)、绝对敌人(既包括内部敌人,也包括外部敌人)。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今天世俗社会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但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模仿宗教的政治模式上走得太远了。救世主、绝对牺牲、“最高指示”、大量印刷的经文般的读物、教礼般的规章、“异端”、受监视的人民……现代“以人为神”的威权主义者们,先是打倒了这些词汇的主人——宗教,然后又把它们拾起来,并入自己的语汇之中。经过一个世纪的瞎折腾,我们才多少有些明白,谁也没有资格代替上帝对别人颁布精神或肉体的诫命。
照朋霍费尔看来,大约从十三世纪开始人类就逐渐地走向自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得到了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神。”但是自律的结果呢?“与此同时,那些基督教神学的种种世俗的衍生物,即那些生存主义哲学和精神治疗学家,就开始乘虚而入,开始介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他们的著述中向自信、 满足和幸福的人类证明,人类其实是不幸的、绝望的,只有他们可以救你脱离困境。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把人们驱入内心的绝望,然后那就成了人们的绝望。它触及了哪些人呢?一小批知识分子,一小批腐化堕落的人,一小批自以为在世界上最重要并因而喜欢盯着自己的人。”
诚然,我们不会忘记宗教裁判所和火刑,不会忘记宗教信仰被赋予国家强制力之后的可怕,但这完全不是要求信仰退出公共领域。到目前为止,不论在科学理论中还是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缺陷却又不产生其他更坏恶果的一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没有发展起来。不仅是人理性的局限,更是人心灵的缺陷,好像真的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终结”;而以个人智识僭越神之身位的任何努力,泰半堕落为“通往奴役之路”。朋霍费尔诗云:
当你起步追寻自由
你得先学会控制你的感觉和心灵
唯恐你泛滥的情欲和四肢
使你偏离当行的路程
操练你的心灵和肉体唯你是从
好奋力追求你所设定的目标
除非你恒守此律
否则永不得认识自由的秘密
当然,马老师还没有如贵国人民一样傻到去相信威权主义可以代替神,他相信的是——“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要传播的东西。我所散布的福音,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在推销怀疑!这就是我的产品。”我不知道他的怀疑是否将他引入了真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怀疑并不能将他引向任何东西。
刘小枫曾生动地描绘了具有高度理性又有高度德性的,信靠着历史理性(换言之,儒家所谓的“天命”)并相信历史理性可以涤荡一切恶的“诗人”。可是,虽然诗人自愿充当了历史王道中的英雄角色,自居为天命的担当者,却不能为自己的不幸和受苦找出理由:儒家学说说明不了,更担当不了仁人善人总是在受苦的事实。儒家把超验的道德价值建立在历史的、政治的(归根结底,人类之性命的)基础上,却没有顾及人类是否真的具有绝对自足性,于是,“要么把诗人逼上了自杀的绝境,要么把诗人推到了荒诞的墙角”,而“恶统统被掩盖在历史的道德形态之中”。“诗人”、君子以为找到了绝对可靠的“天命”,并由此自以为无所不知,最终却只能感叹“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因为人类被罪湮没的历史一再背离这非神性的“天命”。屈原所祈告的“天”是聋的,它只是自然的自在自为的力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如果它真能说话,它说出的一定是《五号屠场》里Tralfamadore星人那句俗语:So it goes.
可见,并非只有西方人秉有与生俱来的欠缺,并非只有西方历史充满了罪恶,并非只有西方人向神发问。区别在于,中国人认识到历史理性的这种欠缺后,却发明出“无所不能”的“圣王”、“英主”,呼召万民的臣服。
那么,认清了人性的欠缺之后,有没有可能就抱残守缺,像尼采所说一样,amor fati,去爱这虚无、偶然、破碎的世界,从没有根基的土地上发出抗争呢?加缪钟情于周而复始地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并断言“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萨特则说生存的“恶心”正说明人应完全“自由”地自在自为,并称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罗素也说过一番激荡人心的话:「人类的产生,是出自一些漫无目的的来由。人类的起源、发展、盼望、恐惧、爱情、信念,完全是原子盲目冲撞的结果。世上没有任何事物,不管是热诚、英雄本色,理性、或感性,能使他超越坟墓而存续。历代的丰功伟迹,鞠躬尽瘁,雄才大略,以及人类天才登峰造极的成果,迟早要与太阳系同归于尽!人类辉煌成就的殿宇,至终必然埋没在宇宙灰烬的荒冢中!……这些说法,就算并非无可置疑,但却确实到一个地步,任何拒绝这些说法的哲学,是站不住脚的。惟有在这些真理的架构中,在这毫不放松的绝望的稳固根基上,人类才能建造他心灵的住处。」
人真能向绝望发起挑战,甚至以此绝望为根基来建立自己的伟业么?刘小枫对这种“荒诞人”犹不以为然,因为:“它赋予世界的荒诞以应然权利,认可世界的事实性的绝对力量,迫使人的精神情怀与之认同,教人们在荒唐的无聊中心安理得,在无耻中不感到羞耻,在冷漠和随便中不感到难受和痛心……理性用自己的限制把上帝贬到最低限度——无聊,又用同样的限制把经验世界的事实性推到形而上学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来,“荒诞人就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结果:理性的局限不是对它自身的限制,反而是对超验的东西的限制、对一切神圣和美好的东西的限制……理性把自己的局限(不理解超理性的东西),偷换为对神圣的东西的限制(与这个世界不相干)。”“明明是这出于虚无的实存情绪的理智之知不要上帝,却又抱怨没有上帝,进而把自己造成的虚无和恶心的后果归于上帝……有缺陷的理智主动拒斥上帝,并把这种拒斥当作自身确立的首要条件,却又把上帝不存在当做自己受苦的原因……现代虚无主义思想家的‘我思’贼喊捉贼。”
换言之,人类应该正视自己的欠然。首先,正因为这欠然限定了人的自由,人便不可能恣意而行;其次,正是这欠然说明了人有超越的使命和可能,因为它是开放的同义词,是“开放着的无”:
过去,现在,将来
我们都是
无,
那无之玫瑰
无所属之玫瑰
开放着。
(策兰:《无所属之玫瑰》,1963)
这“开放着的无”就是人。我们的生命来自无,走向无;但这无不是空无,而是充盈。它是“创造性的无”,是“恩宠的容器”,是舍勒所说的,“超越的意向和姿态”。
即使我们不以这种有点装逼的角度看待信仰,我们也当发现,现实中时刻都有一些问题要远比老马的“为什么要信上帝”更难以回答。假设有好事者询问中国人:你怎么会没有信仰呢?我们可能会更加难堪。前面已说过,人不可能真的没有信仰,嘴上发誓说“我有信仰我就是猪”,只能说明要么你真正的信仰难以启齿(信钱,信权,信黑社会,信凤姐),要么你处于盲信中而不自知。基督徒有个广告老是搬出来用,说中国之所以没有美国及欧洲富饶,皆因欧美信基督之故,这话已经被很多人举非洲拉美的例子给驳斥了。但我弱弱地想,中国在其他方面上隐性的落后,还是有宗教的原因。
清末的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曾很傻很天真地以为,西方文明只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器用之学”,而我天朝虽然贫弱,却颇得孔孟的道德哲学之根本,因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好像说,别看你们现在这么牛逼,不过是些有钱没文化的煤老板;等有一天你们在荒淫中得了花柳奄奄一息,我们就会拿起四书五经去拯救你们,我们才是真正的动感超人,哈哈哈——只可惜这种阿Q的精神只是当年对西方认识不多的产物,自严复等人驳斥后逐渐无人问津。陈寅恪先生反而批评中国文化太重“实用”:“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
早在1920 年2 月1 日,陈独秀就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该文认为,耶稣教给我们的是“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这精神“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我党先驱李大钊也认为:“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蓝公武先生,则著有《宗教建设论》一书,认为“今救中国,舍宗教以外,诚无他途矣。然今之宗教,不一二数,曰儒,曰佛,曰耶,曰回,其教义虽互有异同,而皆足以起人之奉,坚人之信仰……使其而一有效者,则佛可以救国,儒可以救国,即耶、回诸教,亦无一不足以救国。”前面说的寅恪先生,则对佛教大有好感:“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后来既视佛教为垃圾,也视基督为乐色;既没能选择全面保守,也没有选择“全盘西化”,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盘西化——苏联化。(或者说,是苏联化选择了我们囧)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反而看到,似乎中国人才成了那个为利益不惜出卖良心的煤老板,而欧美人关心的**、**和**等“普世价值”,要么被我们视为不怀好意,要么被我们划入敏感词。“民主的细节”,成了离我们很遥远的事,但我们毕竟看到,原来西方以基督精神为代表的道德哲学远不是我们所想的那般孱弱,它没有沦陷在纸醉金迷的工业文明之中,它可以巨浪滔天,也可以润物无声,无数普通人将它薪火相传,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善人都被关入牢狱,孤苦无告时,它仍然不绝地回应着西方人在心灵旷野上的切切呼告,护持着他们爱怜每份穷苦和良善的心,而这一切,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
在《论基督徒》中,汉斯•昆提出了一段我相信任何人都难以辩驳的话:“必须终止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里人民大众被贬低、被蔑视、遭受贫困和剥削;最高的价值是商品价值,货币是真正的上帝,行动的动机是利润、一己利益、自私的目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发挥着宗教代用品的功能。”
这描述的似乎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到今天,各种歌舞升平的盛世假象已经很难掩盖这个大国如索多玛般的内核,更无法搪塞这一事实:“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一个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理念对于中国是合适的,也不知道如何知道什么理念对中国是合适的(赵汀阳)。”威廉•詹姆斯讲,宗教是“个体在孤独的状态中,当他认为自身与其所认定的神圣对象有某种关系时的感觉、行动与经验”。 我们中国人,正是被幸福指数最高,被寂寞指数也最高的一群;那些无奈的事,听多了,看多了,老百姓就学会了健忘,懂得了孤独。说实在的,不想孤独也难,那样就会沦为“不明真相”或“不法分子”的一员。
那么,基督教对于我们是合适的吗?对于中国来说,基督和孔子有些什么不同的意味?上帝和春哥又有哪些不同呢?汉斯•昆曾自我发问道:“基督教面对着后基督教的各种人道主义,有进化论的或者革命的,这些主义也同样支持一切真善美,赞同一切人类价值和博爱,以及自由平等……如果是这样,或者至少应该这样,那么基督教还有什么特殊?”
他说,回答很简单——
一、 基督教的特征是耶稣本身,他不断得到重新的认识被承认为救主。
二、 进化论或革命论的人道主义偶尔地无论怎样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尊敬,甚至把他当作榜样,都不会在人的全部维度中把他视为对人具有最终决定性的、限定性的和原型的意义。
昆老师高屋建瓴,我呢就不一定解释得好这些话的意思,只能大致说说。就儒学来说,孔子的“仁”虽然很有希望成为中国人所能信靠的终极价值,但邓晓芒老师指出,一部《论语》并没有真正地说清楚“仁”是什么(要么答非所问,要么意旨不明,要么过于简单);儒家主要是一套实用性的伦理规范,而且还是一套不够全面的伦理规范。“山上宝训”道:“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确实狠了点,但是“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这种一会论心一会论迹的做法又让民间的道德标准过于灵活而失去制约力。孔子又是一位不容对话的教主,他的学生们只能谦卑地领受他的思想,而不能对他有任何质疑。邓晓芒由此认为,儒家的言说方式只能导向一个父权专制的制度,对信念的依托与对强权的依托成为一体。
而耶稣基督则首先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出现的,舍斯托夫引述路德的话说:“上帝派自己的独生子去尘世,并把一切罪恶加之于他身上,说:你是彼得,一个离经叛道者,你是保罗,一个强暴者和渎神者,你是大卫,一个私通者,你是偷吃天堂之苹果的罪犯,你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你犯了尘世中所有的罪。”从每个人都是欠缺的前提出发,耶稣平等对待每个人,鼓励着每个人与祂对话。
更重要的是,如赵汀阳老师说,“(儒家)只说明了一种社会秩序,却根本没有设计出生活的诱惑和意义。假如一种伦理体系不能蕴涵某种精神性的诱惑,它就不是一种足够好的伦理。儒家最主要的观念是一种父权专制制度,即在家庭的事务上完全服从父亲,在社会事务上完全服从皇帝。这也许是有效的管理方式,可是把人管理好了到底是又想让人去做什么呢?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可能生活?儒家的缺陷正在于它把这种伦理制度本身当成了最高价值,于是,这种伦理观念就不是用来追求其它价值的,而是用来追求伦理自身,这种自相关的伦理是一种严重的理论缺陷,一种不服务于其它精神价值的伦理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而且它实际上压抑了人们关于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的想象和追求。如果没有某种优越的精神追求,规范就没有价值分量,人们所想象的好生活就无非是物质享受。”
儒家找不到真正的精神价值,正是在于它是完全立足于尘世的,而终极价值只能向不可能的地方寻觅,在不可言说的地方言说。就汉斯•昆看来,当现代以来的上帝脱去了天真的、人类学的外衣,祂已不是一种“光明的”、神的映像,而更多地是对现实的一种统一的理解:是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上帝交出的终极价值便是“爱”,祂要求着你以爱来回应。
上帝和春哥的区别正在这里,你没必要信春哥是因为你知道春哥只是个唱歌的,一打开芒果台就能看到,春哥身上没有不可言喻的神性;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并非她的经纪人、老板、作曲者、保姆、亲人、或曾哥,她就对你没有爱。对于没有神性的存在,我们不能去信仰,而只需去认识;如果能以短信方式给她投票,那就做得更到位了。可是上帝是无法认识的,因为祂即使不一定真是全知、全能、全善,祂也必如缪勒(Max Muller)所言:“上帝的概念无论可能是何等的不完善,多么的幼稚,它总是代表了人类灵魂在当时所能把握的无上完善的理想。”
因此,今天我们考察宗教的效能,不会单单去看它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更要看它能指引怎样的实践。王守仁讲知行合一,唯物主义者也鼓掌,因为“不能实践的空想什么的最讨厌了!”可是“行”并不是只能绑在“知”的大腿上,因为人并不都是理性的,理性人是研究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却不会只按理性行事,爱因斯坦指出:“在所有高级的科学工作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信念,即相信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制度善于威慑人让人不做什么,可是只有非理性的爱和希望,才能激励人们做什么,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即是说,很多时候,只有“信”才能导致“行”。对有的信徒来说,救恩是预定的,我的事功并不能换来上帝青眼相看,但是真正理解上帝之恩典的信徒必定会做些事情来改良这个社会,因为“神助自助者”。
在今天的中国,不缺乏真知灼见的人,多数人都知道民主自由是好的,但考虑到自我利益,他们宁可放弃对这些敏感词的追求,因为“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我怎么知道实现民主的赔率是多少?会不会幸福都被你们这些孙子享受了,痛苦都撞我头上了?是以你知得再清楚,仍然不会去行。对更审时度势的人来说,所谓平等、正义、自由,这些概念是根本无法以理性考量来证明的。到最后,再多的被代表和被自杀都已不能让我们动容,最多只会“画个圈圈诅咒你”。而对美国人来说,信仰早已给出确定的依靠了:“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
热衷于死啃《圣经》原本的机要论者和在修道院中终老一生的圣者们已不再是今天教徒的主要面貌。汉斯•昆说:“对上帝的理解的前提是现代意识从注重来世转向注重现在:作为世俗化过程的结果,尘世各种体系的自主性不仅在理论上日益为人所知,而且在实践上也化为现实。但是,放弃来世许诺和更密切注视现世的做法提供了一种机会:生活虽然可能失去了某种深度,但可能增加其强度。”而今天的世界,在克服了宗教专制主义之后,面对着更深刻的堕入世俗主义的危机;上帝对于实践的价值,仍然是祂作为固有的超验的价值。
克尔凯郭尔早已说了,“如果我能客观地把握到上帝,我就不可能有信仰。正是我不能,所以才必须有信仰。”舍斯托夫从他的灵魂里听到了绝望而最可宝贵的旷野呼告,坚信世人要“以头撞墙”。正因为这种真理荒谬,它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我才肯定。
所以,你尽可说,“《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却不能忽视艾略特的信念:
“我们的启示价值论主张:任何书要拥有这种价值的话,必须是在不自主,即不出于作者之自由意志的情况下编撰成,或是主张这种书不能有任何科学或历史的错误,也不能表达任何区域性或个人的情感,否则,《圣经》也许就会在我们手中得到不适当的对待。
相反,如果我们的理论承认:一本书还是可以成为一部启示,虽然含有错误、感情以及人为刻意的创作,只要它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与其命运的危机搏斗之内在经验的真实记录,我们就可以对它作出较为有利的判断。”
哥信的是上帝,不是寂寞。
P.S.1: 请全知全能的友邻们不吝指正。请剽窃者自重。
P.S.2: 豆瓣诸信仰讨论小组对此文亦有贡献。
P.S.3: 还有许多想法此处已无空间吐露,读者诸君,我们还是留待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