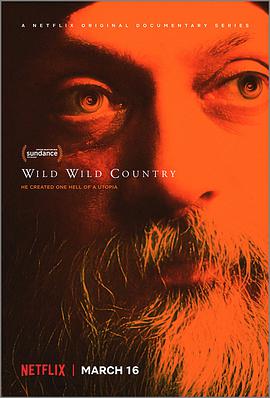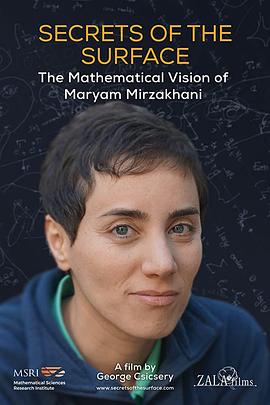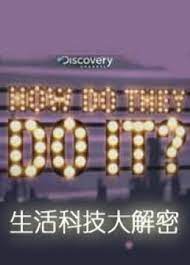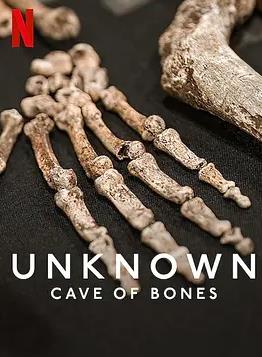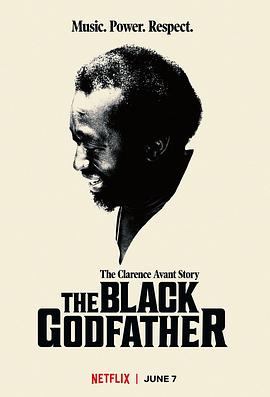爱格尼斯的海滩
- 主演:
- 雅克·德米 塞吉·甘斯布 吉姆·莫里森 阿涅斯·瓦尔达
- 备注:
- DVD版
- 类型:
- 纪录片 纪录片,传记
- 导演:
- 年代:
- 2010
- 地区:
- 欧美
- 更新:
- 1970-01-01 08:00
- 简介:
- 一位年长的老人正在慢慢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充满机智和欢乐的叙述流露出叙述者淡淡的乡愁。 ....详细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268.html
2008年,阿涅斯·瓦尔达已经80岁了,生日那天她打开了门,朋友和邻居进来为她庆祝生日,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扫帚,在法语里,扫帚是年岁的意思,“我是80把扫帚。”阿涅斯·瓦尔达幽默地说,大的小的,长的短的,精致的,简陋的,还有一把正通过邮件寄送过来。当阿涅斯·瓦尔达的院子里放满了倒立着的扫帚,她仿佛看见了自己走过的不同岁月:于是,人倒退着行走,像是从现在从今天从80岁生日倒回到昔日时光;于是,她拿着镜子,镜子里是拿着镜子的瓦尔达,拿着的镜子里是另一个镜子里的瓦尔达。
无数的镜子,无数的瓦尔达,一种增殖,在镜像世界里通向无限,“这些都发生在昨天,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与影响即时融合的感觉,像一切依然存在。”当生命变老,当岁月苍白,镜像却并没有变成一种破碎的存在,和瓦尔达倒走的方式一样,从现在为端点,或许能够以另一种方式看见自己,而一部纪录片作为特殊的镜像,也在字幕之后闪现了“电影还没结束”的提示:那一片街上的人造沙滩,坐在里面织着毛衣的瓦尔达,旁边嬉戏的孩子,似乎都拉回到故事发生的场景中。
电影还没结束,电影其实刚刚开始,而开头就是那一片真正的沙滩,远处是大海,无边无际,近处是赤着脚行走的瓦尔达,一种童心未泯的感觉,似乎正准备远行。为什么是沙滩?因为那是人生的起点,站在沙滩上的瓦尔达说:“当我们翻开一个,会发现风景,而如果翻开我,就会发现海滩。”站在沙滩,是站在80岁的现在,也是站在生命起点的过去。那一片比利时的沙滩,就刻写着瓦尔达关于生命的最初印记,出生在布鲁塞尔,作为家中五个孩子的老三,就是在那片沙滩上拥有了第一种记忆。
而那就是生命的符码,作为老三,瓦尔达在兄弟姐妹的中间,感觉到的是一种独立的感觉,于是18岁时改名的记忆像是独立的一种写照,而这样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却又带来了某些伤感,当海水冲上岸来带走了写着的名字,一种记忆也以脆弱的方式被涂写了:父亲从未说起自己是希腊人,全家只有一张全家福,而若干年后瓦尔达重回布鲁塞尔的家,也只有杂草丛生的花园和斑驳的墙,一切都是模糊的,而对于这种模糊记忆的寻找,瓦尔达所拥有的就是影像。
《扬科叔叔》这部短片无疑是瓦尔达追溯自己家族历史的一次努力,虽然只是在美国参加活动时知道有这样一位叔叔,但是当见面的那一刻,还是让人激动,扬科叔叔告诉她关于父亲的一些历史,依然模糊,依然隐秘,而瓦尔达分明在扬科叔叔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而从这个影子寻找历史,最后也变成了电影里轮盘游戏中倒下的父亲和《家屋风景》中裸着身子的老妇人,“我没有了记忆,也没有了眼泪。”记忆的确飘散了,但是不管是扬科叔叔的影像,还是融入了电影里的元素,瓦尔达都试图拼接这个模糊的人生起点。
是的,就是沙滩,就是翻开自己的沙滩,就是名字被冲走的沙滩,就是记忆起点的沙滩,瓦尔达让工作人员搬来了镜子,大的和小的,方形的和圆形的,或者对着激起浪花的大海,或者对着沙滩,镜子里有大海和波浪,有沙滩和行人,当然更有瓦尔达,更有镜子——镜子里的镜子,镜子里的瓦尔达,在一种多重叙事里,记忆仿佛也变成了讲述者,“这正是我想要的肖像。”不同的角度,里面是不同的风景,是不同的人物,它们像是相互重叠在一起,在错乱中似乎分不清哪里是真实的场景,哪里是一种镜像的存在。
瓦尔达一定是喜欢镜子的迷幻感觉,它让人脱离现在,她更让人抵达迷宫,而时间,人生,记忆,也无非是迷宫一种——镜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但是拿着照相机的瓦尔达为什么把自己框定在没有镜子的画框里?她走进空着的位置,然后背对着大海,朝着镜头后的人拍照,像是一种互文,镜头后面的人是观众,他们看见了镜子,看见了瓦尔达,看见了沙滩,而镜头前的瓦尔达又以相反的方式看见了观众,她成为画框里的存在,却又制造了“拍摄”这个动作,看见和被看见,拍摄和被拍摄,从来不是在一种单一的世界里呈现,它是交错的,是互动的,是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相互投影。
就像现实和电影、现在和记忆,构成了瓦尔达的双重叙事。从“房子与我被战争隔开”而离开布鲁塞尔,到“炮火中逃亡”而来到塞特生活,从“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的短岬村童年,到“仿佛法国是垂直”的“上巴黎去”,从进入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到遇上雅克·德米,从从事电影创作到共建温馨的家园,所有的经历都成为了瓦尔达在现实层面的叙事故事,那里有生活过的码头,有塞特河道上举行的“水上比武”,有在学校里的升旗仪式,有秘密策划的离家出走,有为生活而织鱼网的工作经历……这些记忆是单薄的,也是丰满的,是碎片的,也是深刻的,瓦尔达记得自己布鲁塞尔家对面是一座修道院,记得在塞特的时候遇到三姐妹的邻居,记得那是一个“自由地带”,却没有什么吃的,记得在警报声中躲进地下室,也记得年少是幻想自己进入马戏团。
种种的记忆都组成了瓦尔达关于过去的一种叙事,但一切似乎都模糊了,瓦尔达却说,“模糊的图像,我喜欢。”一张图片里,因为那只手动了一下,所以照片虚焦而看不清了,这是记忆的一种状态,但是瓦尔达喜欢模糊,因为模糊带来的是一种动感,一种不被瞬间定格的可能性,而瓦尔达究其一生都在探寻这种影像的模糊性,都在解读这种具有电影意义的可能性。《短角情事》是她在27岁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关于爱的探讨,一边是渔村人的日常生活,两种叙事平行发展,它们可能交互,可能独立,从福克纳小说中汲取的灵感,似乎就是在对模糊的时间阐述意义;而在新浪潮中,瓦尔达的《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更是直接呈现了一种客观时间,当电影叙事的时间等同于客观时间,其实已经将主观时间融入其中,“我分分秒秒跟随她,电影结合了两种时间。”
“人们都说童年是根基,提供了架构,我不知道,我并没感到跟我的童年有很强的联系,它并不是我思考过程中的参照,它不是灵感。”这是对于客观时间的某种无奈,它会变模糊,它会逝去,但是瓦尔达却用电影创造了另一种时间,它是可能性,它是意义,“25岁之前我只看过10部电影。”但是电影世界打开了,“我只是运用我的想象力,然后投身其中。”从在巴黎学习摄影,到为剧组做照片,从独自一人摄影,到中国、古巴的访问,瓦尔达开始发现模糊的美,开始激发自己的想象,她认识了阿伦·雷乃——《短角情事》里,阿伦·雷乃为电影剪辑;她结识了戈达尔,拍摄了《麦当劳桥上的未婚妻》,“出于友情,他让我拍摄了不戴墨镜的他,我喜欢他美丽的眼睛和他的电影。”当然,对于瓦尔达来说,人生最重要的遇见便是那个叫雅克·德米的男人。
曾经策划了离家出走,曾经坐上了马赛的火车科西嘉的轮船,曾经以修补渔网为生,一个追求独立的女孩,其实是没有安全感,“我紧张,我焦虑,我对男人没有好的印象。”但是,当雅克1德米进入了她的视线,进入了她的生活,她对于男人的那种恐慌和不安全都不见了,1958年相遇,1959年住在一起,那个小岛,那所房子,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即使两个人独自工作独自创作独自拍片,但是最美好的爱情让他们找到了生命最华彩的篇章,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瓦尔达的所有记忆都有了雅克的影子。
他们一起投身在新浪潮运动中,他们在电影世界里革新,他们共赴美国好莱坞寻求合作,他们拥有了女儿和儿子,“一家人在一起,是幸福的总和。”而这一个家,其实就是电影之家,“电影就是我的家,我住在里面。”儿子女儿在电影中成长,而瓦尔达和雅克,也在共有的电影世界中发现生命的意义。雅克不断探索歌舞片的新可能,瓦尔达则在超现实主义诗歌和绘画中寻找灵感,而当五月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不在制作温和的电影,雅克的《小镇房间》直指巴黎的罢工,瓦尔达的《流浪女》探索对社会的叛逆,探索自由的意义,《一个唱,一个不唱》则转向对女性主义的关注,甚至在实践中,瓦尔达也参加游行,也在宣言书里签字,《黑豹党》则聚焦黑人群体争取自身权力。
这些是成长的记忆,是生命的印记,在瓦尔达的世界里散发着模糊的运动之美,但是,记忆并不都是美的,“记忆就像云集于空中的苍蝇,一点记忆,就乱作一团。”对于瓦尔达来说,记忆之可怕不是疾病本身的可怕,而是死亡,人生没有所谓的草图,只有最后的结果:死亡,当那张照片上合影的人都已经死去,瓦尔达禁不住泪水,当她在公墓里看见那些坟墓,她用玫瑰和海棠寄托哀思,而所有的死亡对于她来说,都归结为一种死亡。“所有的死亡都将我引回雅克,每一滴泪,每一束花,每一支玫瑰,每一朵秋海棠,都是献给雅克的花,他是死者中我最珍爱的。”《五点到七点的的克莱奥》中对于癌症的恐惧终于变成了锋利的现实,雅克得了艾滋病,在1989年,这种是一种被视作羞耻的疾病,而瓦尔达却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以相反的方式走近他,记录他,保留他。
《南特的雅克·德米》就是以最近的方式体悟生命,那是雅克的童年岁月,那是德米的电影启蒙,那是南特的“模糊”记忆,瓦尔达在现实中看见了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到那时她要用影像的方式让他活着,“我以极端的特写方式拍摄他的皮肤,他的眼睛,他如风景般的头发,他的手,他的斑点,我需要这样做,记录下这些关于他,关于他的非常状态的影像,雅克死了,但雅克仍活着。拍摄在10月17日结束,雅克于1990年10月27日去世。”10天,隔着现在与记忆,隔着现实与电影,但通向了一种恒久的处所,那就是电影的存在意义,“电影是什么,它是某处的光线,是用来捕捉一切的。”所以瓦尔达建造了电影这个家,而且希望自己一直住着。
从摆满镜子的海滩作为起点,到手拿镜像的院子作为终结,这只是一部两小时记录电影的时间,“时间已逝,并正在逝去,只有海滩是永恒的。”海滩上有镜子,有照片,有孩子,有佛像,有存在永不磨灭的记忆,有制造无限可能的影像。倒走的步履,微笑的面容,80把扫帚的祝福,对于瓦尔达来说,一切都像那片海滩一样,她站在没有镜子的画框里,举着相机,让影像世界在互文和延伸中走向永恒之境,死亡之后,80岁之后,会听到她对大家喊道:“电影还没结束呢!”